黄帝在《内经》开篇里问:“余闻上古之人,春秋皆度百岁,而动作不衰;今时之人,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,时世异耶?将失人之耶?”
岐伯答:“上古之人,其知道者,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,食饮有节,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,故能形与神俱,而尽终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。今时之人不然也,以酒为浆,以妄为常,醉以入房,以欲竭其精,以耗散其真,不知持满,不时御神,务快其心,逆于生乐,起居无节,故半百而衰也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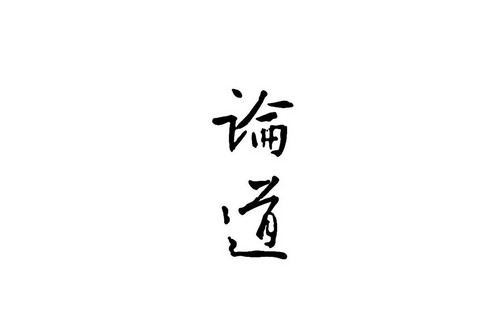
上古之人的生命为什么能够达到百岁?这是黄帝的问题。解释这一问题,岐伯给出了六个理由:第一是知道,第二是法于阴阳,第三是和于术数,第四是食饮有节,第五是起居有常,第六是不妄作劳。请看,养生的第一要务不是求神,不是拜佛,不是吃补品,而是在于知道。
这句话出在《上古天真论》的开端,而《上古天真论》则是《黄帝内经》的开篇第一篇。养生在于知道,这是《黄帝内经》在开篇第一篇中所讲的养生哲理。
诸子百家百家争鸣,对诸子中的六子,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有这样的评价:“《易大传》:‘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。’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。”诸子有一致之处,有百虑之别。一致在何处?一致在道这里。百虑之别在何处?在各家所论证的不同问题中。说明大家所论证的问题不同,但论证问题的方式皆是以道论之。这说明了什么?这说明在此时,道是论证问题、判断是非的终极坐标。
既然由道出发可以演化出百家之术,那么,从这里也可以演化出医理医术。






